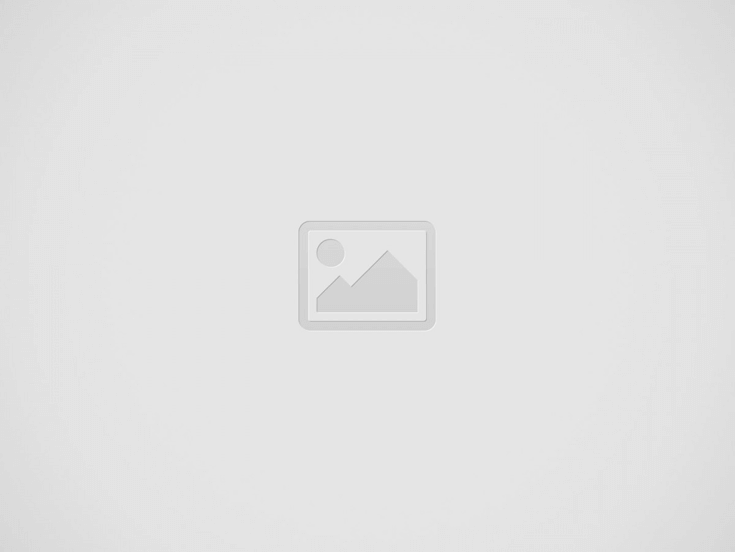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人类适应社会和物质环境的研究。人类适应是指生物和文化过程,使人们能够在给定或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繁殖。这可以在时间上(检查存在于不同时期的实体)或同步地(检查当前系统及其组件)来执行。中心论点是,在小规模或自给自足的社会中,自然环境部分依赖于自然环境,是社会组织和其他人类机构的主要贡献者。在学术领域,当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将经济学视为政体时,它就成为政治生态学的又一学术分支。它还有助于审问复活节岛综合症等历史事件。
定义
“新民族学词典”中的文化生态学定义是:
“……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处理自然(生物和无生命)环境以及文化和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 Walter Hirschberg(ed.):新的民族学词典
管家几乎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术语:“文化生态学是研究社会适应环境的过程。”
特征
它来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学派。作为经济人类学的一门学科,它是第一所开始研究社会与其生存物质基础之间关系的学校。
文化生态学可以通过历时(通过检查不同时间存在的实体)或同步(通过检查现有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来理解。中心论点是,小规模的环境或部分依赖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促进社会组织结构和其他人类机构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那些与社会中财富和权力分配有关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影响囤积或慷慨等行为,例如加拿大西海岸的海达传统的potlatch。
在学术界,当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时,经济学作为政治系统的研究成为政治生态学 – 另一个学术分支学科。它还有助于质疑复活节岛综合症等历史事实。
历史
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1902-1972)创造了这一术语,将文化生态学视为一种理解人类如何适应各种环境的方法论。在他的“文化变迁理论:多元线性进化的方法论”(1955)中,文化生态学代表了“通过适应环境诱导文化变革的方式”。关键的一点是,任何特定的人类适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历史遗传的,涉及允许人们生活在环境中的技术,实践和知识。这意味着虽然环境影响人类适应的特征,但它并不能确定它。通过这种方式,斯图尔德明智地将环境的变幻莫测与占据特定环境的文化的内部运作分开。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环境和文化或多或少是独立的进化轨道,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的能力取决于每个人的结构。正是这种主张 – 物理和生物环境影响文化 – 这已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暗示了一种环境决定论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作的人。文化生态学认识到生态环境在塑造一个地区的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Steward的方法是:
记录用于利用环境谋生的技术和方法。
查看与使用环境相关的人类行为/文化模式。
评估这些行为模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程度(例如,在干旱多发地区,如何对降雨模式的高度关注意味着这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并导致降雨的宗教信仰系统的发展这种信念体系可能不会出现在一个可以将作物的良好降雨量视为理所当然或实行灌溉的社会中。
斯蒂沃德的文化生态概念在20世纪中叶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中广泛流行,尽管他们后来因其环境决定论而受到批评。文化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过程考古学发展的核心原则和驱动因素之一,因为考古学家通过技术框架及其对环境适应的影响来理解文化变迁。
骨架
该研究的主要重点是根据食物和水条件,可用性,气候,限制和限制,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可用性,以及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环境变化,使社会群体适应环境的过程。
因此,这种学科方法主要与文化的唯物主义概念相关联,文化被视为知识系统,允许人们积极地与环境互动,以使生物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这种文化概念的背景是以某种程度的环境决定论为特征的社会系统的愿景,然而,由于技术知识也被认为对适应于社会文化解决方案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解决方案具有影响这一事实得到了缓解。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社会的研究通常更多地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出发,后者的发生率更高,这是由于系统方面的重要性所致。另一方面,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生态平衡随时间的演变的分析是在民族考古研究的支持下进行的,这种研究使我们能够重建过去研究人群的生活条件;这与对Steward和其他提倡所谓“相似复兴”的美国学者所支持的进化人类学的重新评价是一致的,例如Leslie White和Marvin Harris,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接近文化生态学的方法。
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受到批评,因为过度重视那些可能被称为“结构条件”的人,以及过分重视社会生态平衡而牺牲社会变革。然而,它在狩猎和采集等简单社会的研究中产生了有趣的结果。
与类似学科的关系
因此,文化生态学涉及经济人类学的一些主题,但它并不仅仅关注生产领域,而是试图关闭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循环。
随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一些学者提出了这一点,其中最重要的是Roy Rappaport,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子学科:生态人类学。所解决的问题非常相似,但理论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文化被认为是维持生态系统中“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所决定的平衡的功能要素。社会实践的能量分类和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负反馈分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和控制论。
文化生态学不同于政治生态学,因为前者强调适应和动态平衡,政治生态学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失调和不稳定力量的作用。
etnoscienze的一部分被称为etnoecologia,人们对生态方面的看法与他们有关。
过去研究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态条件的尝试将文化生态与考古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研究计划引起了程序考古学。
影响
最初由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设计,文化生态学被许多科学家所占用和改造。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将斯蒂沃德的反思融入经济,然后是政治或精神方面的考虑,以便更好地了解景观随时间的变化。这种理论转变彻底改变了斯图尔德所设想的文化生态,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思想流派:生态人类学。同样,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威尔也通过解释信仰,习俗,以及更普遍的管家否认环境影响的文化领域,与环境相关联,实际上是由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思考文化生态学。简而言之,对于哈里斯及其追随者来说,阿兹特克人的祭祀仪式甚至是中东的猪肉禁令都只是适应特定环境的反应。因此,他证明了印度次大陆牛的神圣性,通过解释后者更有用,这要归功于他的牛奶或他的粪便(可以用作肥料),只能死去给肉。哈里斯特别激进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特别是与美国人类学家辩论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但是,许多考古学家也采用了斯图尔德的理论,他们将文化生态学融入到过程考古学的更广泛反映中,以便解释古代社会的运作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然而,随着科学考古方法的发展和古气候的日益增长的研究,文化生态学的前提已经过验证和验证,使得管家理论变得多余。
总之,文化生态学已经成为许多理论和思潮的基础和灵感,无论是生态人类学,文化唯物主义还是过程考古学,但这种范式也受到了批评和超越。通过新技术的出现。
在人类学
Steward开发的文化生态学是人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它来自Franz Boas的工作,并且已经扩展到涵盖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特别是社会中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以及它如何影响囤积或送礼等行为(例如在北美西北海岸的potlatch)。
作为跨学科项目
一个2000年代的文化生态概念是一种普遍的理论,它将生态学视为一种范式,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也适用于文化研究。在他的DieÖkologiedesWissens(知识生态学)中,Peter Finke解释说,这一理论汇集了历史上演化的各种知识文化,并在现代的演化中被分成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学科和分支学科。科学(Finke 2005)。在这种观点中,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文化领域不是与生态过程和自然能量循环相互分离,而是相互依赖和输入。同时,它承认文化过程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反思动力。由于文化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文化中自然界的不可挽回的存在正在获得跨学科的关注,文化生态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文化进化与自然进化之间的差异。信息和通信不是遗传规律,而是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见Finke 2005,2006)。因此,因果确定性法则严格意义上并不适用于文化,但在生态和文化过程之间仍然存在有效的类比。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是第一个在他的心理生态学(Bateson 1973)的项目中得出这样的类比,该项目基于复杂的动态生命过程的一般原则,例如:反馈循环的概念,他认为在思想和世界之间以及在思想本身之间运作。贝特森认为头脑既不是一种自主的形而上学力量,也不仅仅是大脑的神经功能,而是一种“(人类)有机体与其(自然)环境,主体和客体,文化和自然“,因此”作为与物种生存相关的信息电路控制系统的同义词。“ (Gersdorf / Mayer 2005:9)。
Finke将这些想法与系统理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他将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子系统描述为“文化生态系统”,具有自己的生产,消费和能量减少过程(物理能量和精神能量)。这也适用于艺术和文学的文化生态系统,它们遵循自己内在的选择和自我更新的力量,但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见下一节)。
在文学研究中
文化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一直是文学文化的一个特殊焦点,从神话,仪式,口头故事,传说和童话,田园文学,自然诗歌等流派开始。这一传统中的重要文本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生活相互转化的故事,最着名的收集于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后者在整个文学史和不同文化中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本。这种对文化 – 自然互动的关注在浪漫主义时代变得尤为突出,但仍然是人类经历到现在的文学停滞的特征。
文化与自然,思想与身体,人类与非人类生活的相互开放和象征性的重新联系,以一种整体而又极端多元化的方式,似乎是文学功能和文学知识产生的一种重要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本身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特别强大的“文化生态”形式的象征媒介(Zapf 2002)。文学文本在新的场景中上演和探索了主流文化系统与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的需求和表现之间复杂的反馈关系。从这种自相矛盾的创造性回归行为中,他们得出了创新和文化自我更新的特定力量。
德国生态批评家休伯特·扎普夫认为,文学在与大文化体系的关系中从三重动态中汲取其认知和创造潜力:作为“文化批判的元话语”,“富有想象力的反话”,以及“重新融合的话语”(Zapf 2001) ,2002)。它是一种文本形式,打破僵化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象征性地赋予边缘化的权力,并重新连接文化上分离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文学抵消了解释和工具化人类生活的经济,政治或实用形式,打破了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维观点,向被压抑或被排斥的其他人开放。因此,文学一方面是对社会出现问题的感知,对于片面形式的意识和文明统一的生物麻痹,生命瘫痪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媒介。不断的文化自我更新,其中被忽视的自然能量能够找到一个象征性的表达空间和(重新)融入更大的文化话语生态。这种方法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编辑Zapf 2008,2016)以及最近的专着(Zapf 2016)应用和扩展。
在地理上
在地理方面,文化生态学是响应Carl O. Sauer的“景观形态学”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绍尔的学校被批评为不科学,后来因为持有“具体化”或“超有机”的文化概念。文化生态学应用生态学和系统理论的思想来理解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这些文化生态学家专注于能量和材料的流动,研究文化中的信仰和制度如何规范其与周围的自然生态的交换。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与其他生物体一样,都是生态学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生态形式的重要实践者包括Karl Butzer和David Stoddart。
第二种形式的文化生态学引入了农业经济学的决策理论,特别是受到亚历山大·查亚诺夫和埃斯特·波斯鲁普的作品的启发。这些文化生态学家关心的是人类群体如何决定他们如何利用自然环境。他们特别关注农业集约化问题,改进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博瑟鲁普的竞争模式。第二传统中着名的文化生态学家包括Harold Brookfield和Billie Lee Turner II。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生态受到政治生态学的批评。政治生态学家指责文化生态忽视了他们研究的地方规模系统与全球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如今,很少有地理学家将自我认同为文化生态学家,但文化生态学的思想已被政治生态学,土地变化科学和可持续性科学所采用和建立。
概念观点
人类
关于文化和生态的书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出现。最早在英国出版的是动物学家Anthony Barnett的The Human Species。它出现在1950年 – 副标题为人的生物学,但是关于一个非常狭窄的主题子集。它涉及一些关于健康和疾病,食物,人口规模和质量以及人类及其能力多样性的环境知识的杰出领域的文化影响。巴内特的观点是,他所选择的信息领域“……都是关于哪些知识不仅是可取的,而且对于二十世纪的成年人来说,是必要的”。他接着指出了一些支撑人类生态学的概念,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面对读者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人性不能改变的说法,这种说法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否属实。第三章更详细地讨论了人类遗传学的某些方面。
然后是关于人类进化的五章,以及今天与人口增长(“人类多样性”主题)相关的男性(或种族)群体之间以及个体男女之间的差异。最后,有一系列关于人口各方面的章节(“生与死”的主题)。像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人类必须克服饥饿和感染的危险;同时他必须是肥沃的。因此,有四章涉及食物,疾病以及人口的增长和衰退。
巴内特预计他的个人计划可能会受到批评,理由是它忽略了人类特征的描述,这种特征使人类最清楚地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说人类行为被忽略来表达这一观点;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说人类心理被遗漏,或者没有考虑到人类的思想。他证明了自己有限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不是因为遗漏的内容很少被重视,而是因为省略的主题非常重要,每个人都需要一本类似大小的书,即使是简要帐户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作者被嵌入了一个学术专家的世界,因此有点担心对智人的动物学采取部分概念和特殊的观点。
生态
北美也开始着手制定将人类文化调整为生态现实的处方。保罗西尔斯在他1957年在俄勒冈大学举行的康登讲座中题为“人类的生态学”,他强制要求“认真关注人的生态”,并要求“巧妙地应用于人类事务”。西尔斯是少数几位成功为流行观众写作的着名生态学家之一。西尔斯记录了美国农民在创造导致灾难性沙尘暴的条件方面所犯的错误。这本书为美国的土壤保持运动提供了动力。
对自然的影响
在同一时间是J.A. Lauwery的“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是1969年出版的“自然界中的相互依存”系列的一部分.Russel和Lauwerys的书籍都是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尽管没有这样的标题。人们仍然难以逃脱他们的标签。 1970年由博学家动物学家Lancelot Hogben制作的偶数起源和失误,以及字幕前科学开始的副标题,坚持将人类学作为传统的参考点。然而,它的倾向清楚地表明,“文化生态学”将是一个更恰当的标题,涵盖他对早期社会如何通过工具,技术和社会群体适应环境的广泛描述。 1973年,物理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创作了“人类的崛起”(The Ascent of Man),其中总结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十三部关于人类塑造地球及其未来的各种方式的电视连续剧。
改变地球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类生态功能观已占上风。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方式,以人类动物的生态视角呈现科学概念,主导人口过剩的世界,其实际目的是产生更环保的文化。这是IG西蒙斯的“改变地球的面孔”一书的例证,它的副标题是“文化,环境历史”,发表于1989年。西蒙斯是一名地理学家,他的书是对WL托马斯编辑的影响的致敬。收藏,男人在1956年出现的“改变地球面貌”中的角色。
西蒙斯的书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跨学科文化/环境出版物之一,它引发了地理学方面的危机,涉及其主题,学术分部和边界。通过正式采用概念框架作为促进组织研究和教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跨越旧的学科划分。事实上,文化生态学是一个概念性的舞台,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社会学家,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从他们的专业科目的边缘进入了共同的知识分子领域。
21世纪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一些出版物涉及人类与环境建立更可接受的文化关系的方式。一个例子是神圣生态学,这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子主题,由Fikret Berkes于1999年制作。它从加拿大北部的传统生活方式中汲取教训,为城市居民塑造新的环境感知。人与环境的这种特殊概念来自各种文化层面的当地物种和地点知识,利用当地经验的资源管理系统,社会机构及其规则和行为准则,以及通过宗教,道德和广泛定义的信仰体系的世界观。 。
尽管信息概念存在差异,但所有出版物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文化是专注于开采自然资源的思维模式与保护自然资源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平衡行为。自相矛盾的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生态学的最佳模式可能是欧洲人压制古老的土着土地使用方法并试图将土地上的欧洲农耕文化解决在明显无法支持他们的土壤上时所发生的文化和生态的错配。 。有一种与环境意识相关的神圣生态,文化生态学的任务是激发城市居民与支持他们的环境建立一种更可接受的可持续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