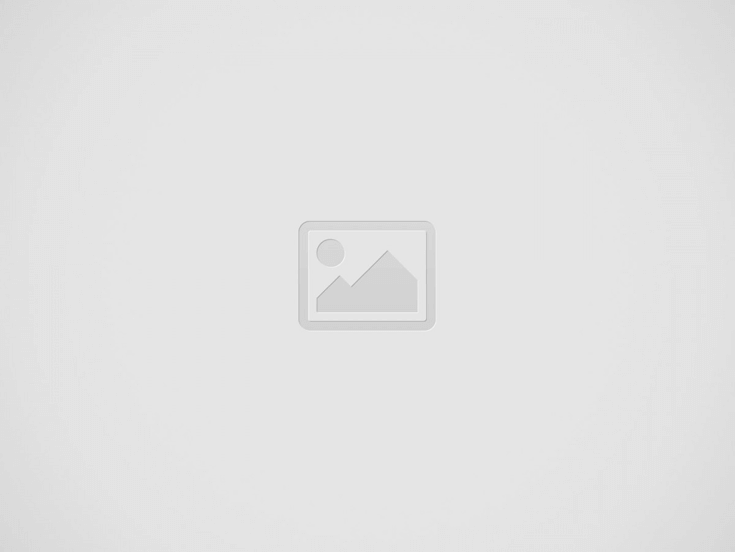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厌恶是与厌恶有关的强烈厌恶感的名称。 与其他不那么严重的拒绝形式不同,厌恶表达的有时是强烈的身体反应,如恶心和呕吐,出汗,血压下降直至昏厥。 从科学上讲,厌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本能。 对于某些气味,味道和异象,本能反应是天生的。 在获得社会化的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的厌恶感。 厌恶有助于预防疾病。 营养禁忌也受到尊重,因为禁忌的潜在食物会导致恶心的厌恶感。
根据曾经处理厌恶的社会科学和文化历史方面的Lothar Penning的观点,厌恶被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在文化条件和教学上传达,利用原始的突破和呕吐反射,获得预先理性以保护基本的社会认同。“
厌恶也会在一些恐惧症中发挥作用,但恐惧症的基本特征是恐惧,而不是厌恶。 极度恶心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特质。 另一方面,在患有亨廷顿氏病的情况下,受影响的人根本不会感到任何厌恶,并且不再能够解释其他人的相应面部表情。
文化史
即使在文化空间内,厌恶也不是文化历史的常客。 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在他的“文明进程”一书中指出,今天欧洲的“体面行为”观念在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中世纪的演变,其表现形式是控制过程中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身体需求变得更加重要。 这个过程从贵族开始,逐渐成为整体社会标准。 伊莱亚斯使用消息来源,特别是桌面消息来表现出几个世纪以来的羞耻感和尴尬感,这相当于厌恶敏感度的增加。
贵族只在现代使用手帕,然后通常的做法是吹手,然后在衣服上擦拭。 通常只使用贵族可用的桌布,但在15世纪,这已被认为是不忠实的。 吃东西时,你应该左手吹,因为你用右手吃(叉子是在16世纪逐渐引入的)。
在一个中世纪的餐桌品种中,它说“不要在桌子上或桌子上吐”,“如果你洗手,不要在盆里吐”。 即使在他人面前或在吃饭的时候,吐痰本身也不会受到反对。 在桌子下面或后面吐痰被认为是体面的。 经常吐出唾液被认为是必要的。 在十七世纪,在优越的人面前吐痰在地球上是不恰当的; 在十八世纪,人们要求使用手帕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在房子里面是上层痰盂常见的。 在19世纪,英语引用说:“随地吐痰是一种恶心的习惯”(吐痰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
根据伊莱亚斯的说法,卫生概念与随地吐痰的禁忌无关,因为这几乎没有被引用作为理由。 “在人们对通过痰液传播某些病原体有任何明确的认识之前,尴尬和厌恶的感觉也会增加痰液的分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动机早在科学见解的动机之前就存在了。”几个世纪以来,对他人身体分泌物的敏感性明显增加。 然而,在许多亚洲国家,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仍然很普遍,并没有引起厌恶。
其他身体排泄物长期以来都不被认为是恶心的。 正如消息来源所证明的那样,所有摊位都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的一篇文章中,它写着“Incivile est eum salutare,qui reddit urinam aut alvum exonerat”(对于那些只是小便或放松的人来说,这是不礼貌的)。 当时在16世纪新出现的压制Flatulenzen的规则,他认为不合适,因为那不健康。 预计17世纪初,没有证人的排便是秘密进行的。 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皇帝和国王,他们经常坐在所谓的“Leibstuhl”中,并将观众视为特别的恩惠。
然后,在1729年,一位法国作家宣称:“Ilesttrèsinvivilde laisser sortir des vents de son corps,soit par haut,soit par bas,quan mesme ce seroit sans faire aucun bruit,lorsqu’on est en compagnie。” (让你的身体在其他空气中逃逸是非常不文明的,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即使它是静默发生的)。 伊莱亚斯注意到在处理所有本能话语时越来越敏感,新引入的行为规则首先具有社会分化的功能,社会优越与“人”的区别。
一般来说,欧洲的气味耐受性曾经比现在大得多,并且长期以来没有特别注意气味。 阿兰科尔宾描述了卢梭时期巴黎的情况:“粪便随处可见,在大街上,在转弯处的脚下,在出租车里.Kloakenentleerer污染了街道;为了拯救他们前往Schindanger的路,他们只是将桶倒入排水沟中。工厂和制革厂也在增加尿量方面发挥作用。巴黎房屋的外墙被尿液分解。
气味和恶臭只在18世纪公开讨论过。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将这一过程强化为’嗅觉革命’,作为对气味的感知,评价和解释的根本改变。特征是不断增长的集体对各种气味的敏感性虽然气味的强度和外显率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改变,但容忍阈值几乎突然下降,到目前为止所有被认为是正常的 – 身体,生活空间和城市的气味,粪便和粪便的气味,臭山等等 – 现在被认为是无法忍受的。“
新气味反应的背景和相关的恶心反应是当时出现的科学嗅觉理论以及强烈气味是病原体携带者的假设,这意味着单独的气味可能导致疾病。 这导致了清洁和卫生概念的根本改变,并努力“清洁”空气。 与此同时,人们对身体气味的感知有所厌恶,无论是自己的气味还是其他气味。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与“普通人”不同,上层阶级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自己的气味,或者通过使用芳香剂,身体气味成为社会的差异化因素。
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屠宰牲畜及其加工成肉类和香肠产品基本上都是公开的。 几乎没有人在视线中冒犯。 直到19世纪,屠宰场才被重新安置到城市的郊区,据社会学家称,这种情况与高度厌恶感有关。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整体上只准备在板上雕刻的准备好的动物也是不寻常的。 1894年的法国食谱指出:“凭借巧妙的装饰或精致的烹饪方法隐藏肉块的残酷外观,烹饪肯定有助于改善习俗。将我称之为”血腥庭院的国家“与“调味品的国家”,然后看看后者是不是更文明。“
文化差异
因为厌恶部分是社会条件的结果,所以厌恶的对象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美国人“更有可能将厌恶的感觉与限制一个人的权利或降低一个人的尊严的行为联系起来”,而日本人“更有可能将厌恶的感觉与阻碍他们融入社会世界的行为联系起来”。
被解释为社会可接受的实践也可以通过其他文化的厌恶反应来满足。 例如,来自满族少数民族的母亲,不仅仅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北满洲的Aigun进行研究,而研究员SM Shirokogoroff个人认为满族元素比南满洲和北京更“纯洁”。通过对他们的男婴进行口交,将阴茎放入口中并刺激他们来表达对孩子的喜爱,而满族则认为公众接吻时会有反感。 此外,中国和越南文化直接倡导消费人胎盘。 建议中国哺乳母亲将胎盘煮沸并饮用肉汤以改善牛奶的质量。 同样,中国人也为了健康目的而消费牛阴茎汤。
厌恶是多种文化中可识别的基本情感之一,是对通常涉及味觉或视觉的反感的回应。 虽然不同的文化发现不同的东西令人厌恶,但对于怪诞的东西的反应在每种文化中都是一样的。 人们和他们在厌恶领域的情绪反应保持不变。
厌恶文学
古
古代的拉丁诗歌包含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描述,通常是在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即使没有与这种情感完全对应的拉丁术语。 有一个术语fastidium具有厌倦的含义,taedium具有极度厌倦的内涵和恶心的身体恶心。
虽然维吉尔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剧烈的影响,但它们出现在奥维德,但几乎完全在他的作品“变形记”中。 在半人马的战斗中,他详细描述了各种伤口和残割。 “凭借塞内卡,罗马诗歌中可怕的写照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塞内卡是斯多葛派; 这些描述与他的任务是明确他的英雄的冷静,这是不能被厌恶打败的。 在他的悲剧中,经常出现的动机是人体的伤害和破坏。 最戏剧性的场景可以在他的作品Thyestes中找到。 重点是对Atreus儿子的祭祀屠杀以及他们如何准备作为一顿饭的描述。
“没有罗马文学的作品像Pharsalia Lukans那样富有可怕和恶心的游戏.Lukan的历史史诗几乎看起来像是罗马恐怖传统的储藏。”Pharsalos之战和罗马共和国的垮台被描绘出来。 两部分专门讨论尸体的腐烂,以及蛇咬伤造成的残酷死亡情景的详细说明等等。 一个。 身体逐渐消失。 Statius和Silius Italicus的作品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动机中放纵了一点,并且与奥维德的关系更加紧密。
现代文学
令人作呕的动机可以在前现代文学中找到,但更多的是怪诞的形式。 一个例子是FrançoisRabelais的Gargantua和Pantagruel,其中尿液,粪便和身体分泌物起作用。 然而,作者并不想挑起厌恶,而是努力争取“释放笑声的效果”。 这些图案的文学处理方式与伏尔泰有所不同,伏尔泰有意识地将Candide描绘成丑陋的,令人厌恶的是与theodicy的观念相对立,其中甚至邪恶总是有意义的。 引文:“第二天他去散步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乞丐,上面覆盖着脓脓的乞丐,眼睛熄灭,鼻子啃鼻子,嘴巴弯曲,还有黑色的牙齿残端,每个人都要嘶哑地嘶哑;可怕的咳嗽适合折磨他,每次都吐出一颗牙齿。“
Heinrich von Kleist也可以找到与“美术”传统的突破。 “Penthesilea(1808)是文学极端主义的第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戏剧不想引起更多的恐惧和怜悯,而是通过厌恶引发宣泄。后来的19世纪作者,首先想到的是浪漫主义者,不小心变得极端。“
自然主义的文学方向处理社会问题,也代表疾病,酗酒和身体退化,恶心的动机被接受为挑衅和批评的手段。 主要人物是ÉmileZola,德国最重要的代表是Gerhart Hauptmann。
在法国,Georges Bataille,Charles Baudelaire,ComtedeLautréamont,Paul Verlaine和Arthur Rimbaud都是现代作家之一,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禁忌。 驱虫剂由它们自己处理,以其“野蛮和动物”来描述生命。 波德莱尔Les Fleurs du Mal引发了一起丑闻并导致了一起刑事案件。
针对厌恶效应也是表现主义的代表,如Gottfried Benn,Georg Trakl和Hans Henny Jahnn。 “从审美角度来说,极端分子专门研究文学规范和语言规则的破坏。与他古怪的语言配对是对禁忌或流行的偏好”。 Trakl主题在他的诗歌衰败,腐朽和死亡,以及医疗Benn。 Jahnn的戏剧牧师Ephraim Magnus(1919)“是一个特殊的暴行和恐怖的存储库,由于诸如恋尸癖,同类相食,阉割,亵渎,乱伦和腐朽等主题的极端积累而无与伦比.Jahnn的戏剧基于反对在Penthesilea之后,厌恶的美学效果就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明显。“
厌恶也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因此,扎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就是如此。 据说,扎拉图斯特拉在这里是预期的超人的先驱,而且这个人毫无厌恶。 然而,在一个场景中,他设定了他的“糟糕的思想”,并在惊叹中打破了它:“厌恶,厌恶,厌恶 – 对我来说有祸了!” 在这篇文章中,一次又一次令人厌恶的主题,它将“吐痰的整个比喻,扼杀”呕吐,包括所有的粪便陪审团 – 整个世界的fie – 努力。“任何厌恶的克服都被尼采描绘成一个许多声明表明,哲学家本人非常恶心,他委婉地将其重新解释为“超敏感性”。尼采对人类普通的普通低地的厌恶已经可以在早期的工作中找到,同样来自于厌恶的转移。道德世界的生理。“他写道:”我对清洁本能非常烦躁,所以我闻到生理上最内心,每个人的’胆量’如果我是正确的观察,那我的清洁和冷漠的自然也感受到了我对他们的厌恶的谨慎对人们的厌恶,“暴徒”总是我最大的危险。“
作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用私人信件和个人厌恶感记录表达了自己。 作为一个主题,这种情感在他的故事“变形”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其中主角一夜之间变成昆虫(“害虫”),于是家庭对恐怖和厌恶感作出反应。
在20世纪的德语文学中,经常讨论厌恶,尤其是奥地利作家。 “自从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歌以来,丑陋和令人厌恶的演出已经成为文学现代主义的核心主题,在二十世纪的奥地利文学中几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来。” 典型的代表是Thomas Bernhard,Josef Winkler,Werner Schwab和Elfriede Jelinek。 在她的作品中有许多禁忌,以“暴力言辞”(令人兴奋的言论)的方式表现,它也想要攻击读者的身体。
法国哲学家让 – 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写了一部名为“厌恶(Lanususé)”的小说,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文学杰作。 主角的厌恶基本上是针对任何存在的假设无用和不确定性。 Daseinsekel或Weltekel称纯粹属于厌恶的名字。 所描述的主角Antoine Roquentin的感受在心理学中被赋予,然而,忧郁和其他在抑郁症中发生。 “忧郁可以从存在主义的分析观点来描述如下:一方面是人类与自己,另一方面和事物的异化,另一方面是对存在的抑制,即作为对存在的关系的修改时间,暂时性。“ 这种异化是罗钦汀病情的基本特征。 萨特最初想把这部小说称为忧郁症。
分阶段厌恶
不仅美丽,而且恐怖和怪诞一直被描绘在文学和艺术中,虽然不一定是为了引起厌恶。 “在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中,令人作呕的表现形式是针对古典艺术的美丽外观。美的审美与挑衅的美学审美并置。”在十八世纪新兴的美学理论中,丑陋和恶心起初完全被忽视了。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将厌恶视为一种矛盾的情绪,基于婴儿对粪便的最初兴趣,他只是在社会化的帮助下断绝了。 因此,前者的“欲望对象”被转化为不满和厌恶的对象。 然而,在无意识的层面中,根据这一理论,被压抑的魅力被保留并以掩盖的形式重复出现。 “受虐狂的个人做了类似于可怕或恶心的艺术表现的读者或观者。他们可以被不幸运动的物体神奇地吸引。隐藏的快乐源泉是满足于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惩罚被禁止的惩罚欲望和冲动。“艺术领域的阶级厌恶的阵风在社会上得到了接受。 公众对禁忌违规行为的愤慨通常只针对各自的艺术家,而不是针对接受者。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观众自愿将自己置于恶心和临时之外,以便建立一定的内在距离,特别是在电影,戏剧或绘画领域。
根据Thomas Anz的说法,“恶心”也满足了其他(无意识)的需求。 “关于世界末日比例的集体灾难的幻想,在艺术和文学史上总是与令人厌恶的幻想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符合宗教末日传统中的道德和侵略性需求。”
现代艺术
对厌恶感的有意识的挑衅是现代艺术不同方向的一种手段,主要用于表演。 厌恶通常是由使用体液和产品引起的,这些产品被宣称为“艺术材料”。 这样做会违反社会禁忌。 众所周知的是所谓的维也纳行动主义。 身体艺术作为动作艺术和吃艺术的一种形式使用部分令人作呕的效果。 艺术家们自己承认,他们希望表达对社会约束和价值观的抗议。
除此之外,维也纳的行动主义者宣称他们想要一种特殊的表达强度和观众的压倒性,这只能通过直接的物理干预来实现。 1968年维也纳大学礼堂里最着名的外观是公开排尿,排便和呕吐,并在其间唱奥地利国歌。 它即将显示“人们对于当时战争的越南战争的所有报道都比较沮丧。” 维也纳行动主义者在接下来的时期中最受欢迎的是Hermann Nitschwho,在他的表演中,让很多动物血液流动。 他公开屠宰动物,然后涂抹血液和内脏画布和人。 此外,他通过在画布上运行血液创造了“Schüttbilder”。 在20世纪70年代初,Nitsch转向剧院,从那时起经常进行所谓的“狂欢 – 神秘游戏”。 他撰写了一篇关于他的艺术的综合理论论文,并提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 他的表演的目标是神经症的解散和宣泄。
受维也纳动作主义的影响是保罗麦卡锡的表演,故意关注恶心的影响。 例如,在1975年,他制作了他的视频Sailor’s Meat,其中McCarthy用金色女人的假发和内裤做了一番,并在番茄酱,蛋黄酱和生肉的帮助下涂抹了28分钟,他先咀嚼然后再吐出来。 他还处理了一个假阳具,并将其浸入蛋黄酱中。 自我染色是人体艺术的风格设备。 “如果麦卡锡拥有典型的美国产品的排泄物,如番茄酱,蛋黄酱,身体霜或热狗混合成一种可怕的酱汁,它就会攻击社会清洁的概念。”
粪便通常用于“恶心的艺术”。 特别着名的是Piero Manzoni的Merda d’Artista(“艺术家的狗屎”)。 据称,1961年5月,他用自己的粪便填充了90个罐头,编号并签名,并提供相当于30克黄金的罐头。 今天的罐头具有很高的收集价值,目前还不清楚其实际内容是什么。 厌恶完全基于这个想法。 Wim Delvoye建造了一个名为CloacaIt的机械物体,它在生物反应器的帮助下模拟了消化过程,并在食物喂养后消除了人工粪便,这些物质与化学真正的粪便物质相似。 这些排泄物现在由收藏家购买。
甚至死亡的动物也被用于现代艺术中以引起厌恶。 Damien Hirst用甲醛制作动物尸体并展示它们。 最着名的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镶嵌的虎鲨,它现在开始腐烂,因为它不能永久保存。 奥地利动作艺术家Wolfgang Flatzmade于2001年在媒体上发起了一场名为“肉食”的行动,当他从柏林的一架直升机上扔下一头死牛时。 撞击之后,几个鞭炮爆炸了。 Flatz在基督姿势的行动期间挂在建筑起重机上。 据他说,他想指出社会与肉类主题之间的不安关系。 维也纳行动主义的影响是清晰可辨的。
腐烂,腐败和腐败也是现代艺术的主题。 Dieter Roth故意制造食物发霉的物体,英国人Sam Taylor-Wood在快速动作的视频中也是如此。 故意使用恶心影响的摄影师包括Joel-Peter Witkin和Cindy Sherman。
在他关于美学理论的论文中,西奥多·阿多诺已经建立了对现代艺术的普遍偏爱,因为它令人作呕和身体上令人厌恶。 他认为这表明了“起诉”社会的倾向,并通过示范性地表达被拒绝和压抑的方式来“谴责世界”。
现代剧院
与此同时,赫尔曼·尼奇主要将他的行动艺术转移到剧院。 他经常在奥地利自己的城堡中进行所谓的狂欢神秘游戏,在这些游戏中,屠宰的动物都被消灭,并伴有管弦乐的声音。 Nitsch整合了宗教祭祀仪式和基督教仪式的元素。 2005年,他被允许在着名的维也纳城堡剧院首次演出。
现代德国导演剧院现在也经常使用血液和其他体液,这导致戏剧评论家形成关键词令人作呕的戏剧,并且最近引发了对德国戏剧的争议性讨论,所有国家印刷媒体都参与其中。 “目前正在讨论德国舞台上的演员是否经常呕吐,小便和手淫,或做更可怕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戏剧就是这样。“导演Christoph Schlingensief被认为是这个方向的”先驱者“之一。 2006年在柏林和汉堡的大舞台上抹去了JürgenGoschin杜塞尔多夫的麦克白生产演员的粪便和假血,还有血液和尿液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表演。
引人注目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风格只在德语国家举行。 导演尼古拉斯·斯蒂曼用德国戏剧的自我形象解释了这一点,德国剧院认为自己是政治性的:“对我们来说,自从布莱希特以来,它一直是为了赢得社会的政治话语和使用剧院。或者自席勒以来。”斯蒂芬·金米格指出在每个犯罪现场都可以看到比在剧院舞台上更多的血和暴力。
电影
1965年,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排斥(拒绝/辩护)在德国以“厌恶”为标题出现,但英文标题更能体现内容。 主角卡罗尔无法忍受男人的亲密和触摸,她的防御具有恐惧和神经质的特征,并且增加了仇恨; 她的厌恶感是她精神错乱的一部分。 观众的厌恶激发了一个切碎的兔子头,卡罗尔放在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在公寓里慢慢腐烂的兔子烤。
恐怖电影通常依赖于恶心的影响,但在这种类型之外它们并不常见。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特殊的类别是所谓的Splatter,其特点是在许多国家特别过度暴露暴力并被禁止。 在电影中,当违反禁忌时通常会发生厌恶,尽管不必总是明确地证明这一点。 同类相食是非常忌讳的,而且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吃人肉的场景的电影很可耻。 例如Pier Polo Pasolini的Pigsty(1968)和Jean-Luc Godard的Weekend(1967)。 在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爱人彼得格林纳威(1989年)的同类相食只是众多禁忌之一; 在这里,一个男人终于准备好了蔬菜和草药的烤肉。
在黑色喜剧“玫瑰战争”中,一位妻子报复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因为吃了一块肉棒而跑过她的猫,她在吃完饭后告诉他,她已经处理了他的狗。 准备工作不明显。 来自香港的导演Fruit Chan于2002年拍摄了一部名为“公共厕所”的电影,并于2004年拍摄了一部题为“令人厌恶的问题”的电影。 饺子是中国饺子。 在陈的电影中,中国人承诺通过她非常特别的饺子帮助女性获得永恒的美丽和青春。 在电影的过程中,很明显填充物基本上由流产的胚胎组成。 在中国,这部电影没有放映。 陈在接受采访时暗示,这部电影的主题有一个真实的背景。
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Buñuel)在他的许多电影中以令人厌恶和令人作呕的方式侵犯了社会上的禁忌。 他在晚期工作中提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头脑:自由的幽灵:这里举行了一场晚宴,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倒进厕所。 在这两者之间,个人道歉在一个内阁偷一口。
电视
在电视节目中也有意使用厌恶。 在1973年A Heart and a Soul广播系列的第12集中,主角“厌恶阿尔弗雷德”在马铃薯碗中引起了一场足浴。 后来,观众所引起的厌恶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所谓的真人秀节目中。 早在1996年,Glücksritter节目成为头条新闻。 在德国,2004 RTL播出我是明星 – 让我离开这里! 进行激烈的公众讨论。 媒体谈到“令人厌恶的电视”; 当时,创造一词是第五届选举中的年度词。在这个真人秀节目中,或多或少突出的参与者在澳大利亚丛林的一个营地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们每天全天候拍摄。 对于高收视率和激烈的批评提供了定期的“勇气考验”。 例如,DanielKüblböck不得不在数千只蟑螂中“沐浴”几分钟。 该节目达到数百万观众,市场份额超过30%。 德国记者协会主席迈克尔·康肯谈到了“电视娱乐的低点”和“偷窥变态”,其中Ekelgrenze将超过。
尽管对丛林阵营的批评,RTL在一段时间之后发出了令人厌恶的格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节目恐惧因素,自2001年以来在NBC美国站播出非常成功。 除此之外,美国候选人不得不吃蠕虫和牛眼,被放入一个装有蛇的容器中或被400只老鼠覆盖。 类似的广播也在其他国家播出,主要是收视率高。
“恶心的电视”的延续是题为尸检 – RTL 2的神秘死亡的系列。“伪装成一系列关于犯罪学家和法医科学家工作的文件,各种各样的尸体都出现在每个可以想象的腐烂和溶解阶段。而且都是真的。“还有尸检。 在14至29岁的主要目标群体中,该节目的收视率达到13%。 “这种关于死亡,死亡和分解的激进和公开连续的报道可能还没有出现在电视上。” 根据记者Oliver Pfohlmann的说法,观众的兴趣既包括对紧张的渴望,也包括“以虐待狂的比例窥淫癖”。 该计划是“勇气的虚拟考验”。
媒体研究人员解释了现实节目的整体成功相似。 根据研究,这些形式主要受“偷窥者倾向”的青睐,因此教育水平不起作用。 “对于非恐惧的观众来说,窥淫癖会导致强烈的娱乐体验。相比之下,焦虑的接受者试图通过查看相关内容来克服自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