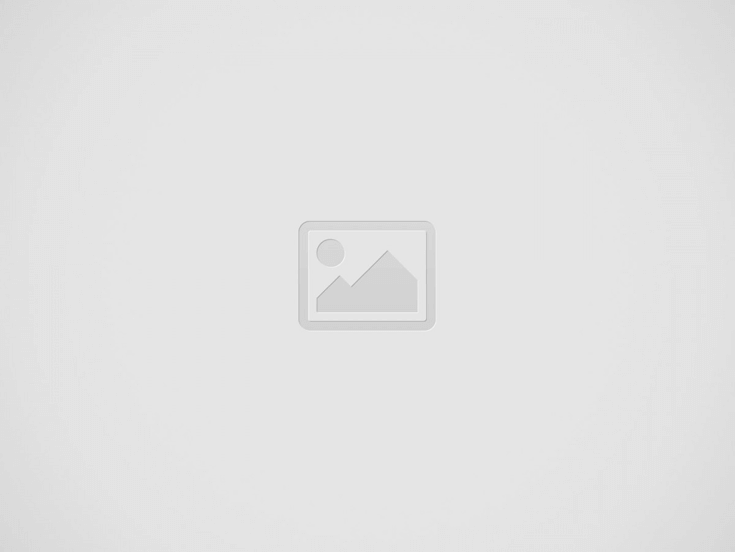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是对居住在不同地点的不同人群如何理解周围的生态系统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研究。
民族生态学研究基于多学科的观点,这些观点基于自然科学和人类群体的行为,发展中人民的观点以及工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观点。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例如生态退化,气候变化,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水资源短缺,经济不平等,甚至人口转变
可以说,民族生态学侧重于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但是却是相互关联的:信仰或宇宙观的体系,知识或认知体系的集合以及生产实践的集合,包括自然资源的不同使用。因此,人类生态学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和方法,用于对人类挪用自然过程的整体研究。基于对地球上不同栖息地的无数文化进行的众多民族生态学研究,有可能确立现代世界土著人民对自然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构想,认识和使用时这些形态的一般特征。
它寻求对我们作为人类如何与环境互动以及这些复杂关系如何随着时间而得以维持的有效,可靠的理解。
民族生态学致力于评估有关地球上土著和农村人口本质的千禧世代知识。可以区分出两种形成了对自然的理解的知识传统:西方现代科学的伪造者和另一种被称为传统经验的伪造者,它汇集了对自然世界的各种形式的理解。因此,有可能区分两种生态,不仅是现代科学组织的生态,而且使成千上万的抵制工业世界扩张和维持行星生态系统的土著文化的生态变得不透明。要使它们可见,需要批判性思维,以提供民族生态学的外观。
民族生态学中的“ ethno”(见民族学)前缀表示对某人的本地化研究,并与生态学一起表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经验。生态学是对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民族生态学对此问题应用了以人为本的方法。该领域的发展在于应用本土植物学知识并将其置于全球范围内。
历史
人类生态学始于休·波普诺(Dr. Hugh Popenoe)的早期工作,休·波普诺(Dr. Hugh Popenoe)是农艺师和热带土壤科学家,曾与佛罗里达大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合作。Popenoe还与认知人类学家Harold Conklin博士合作,他在东南亚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
哈罗德·康克林(Harold Conklin)在其1954年的论文“哈努努文化与植物世界的关系”中,当他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民族生态学”时,创造了“民族生态学”一词。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继续在Hanunoo中进行研究。
1955年,康克林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民族生态学研究。他的“ Hanunoo颜色类别”研究帮助学者们了解了分类系统与文化中世界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此实验中,Conklin发现,由于其独特的分类系统,各种文化中的人们对颜色的认识不同。在他的结果中,他发现Hanunoo使用了两种颜色。第一级包括四个基本的颜色术语:黑暗,明暗,发红和绿色。而第二级则更抽象,由数百种颜色分类组成,例如:对象的纹理,光泽和湿度也用于对对象进行分类。
其他人类学家很难理解这种颜色分类系统,因为他们经常将自己的颜色标准概念应用于Hanunoo。孔克林的研究不仅是民族生态学的突破,而且还有助于发展这样一种观念,即其他文化以自己的方式将世界概念化,这有助于减少西方文化者的民族主义观点。诸如柏林,Breedlove和Raven之类的其他学者努力学习更多有关其他环境分类系统的信息,并将其与西方科学分类法进行比较。
发展
民族生态学方法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像Roy Rappaport这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它位于地理,景观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中,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规范。在这方面,民族植物学(植物(植物学)与人类使用植物有关的研究科学)是民族生态学的一个子方面。为了识别使用系统,它经常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使用合成生态学方法。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一个子方面导致了人类生态学工作的广泛研究和应用。它于1992年引入了获取和惠益分享(ABS)机制,即“获取遗传资源和平等惠益分享”。除了获取遗传资源外,获取和惠益分享还涉及公平分享使用这些资源的惠益。像《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其他规定一样,获取和惠益分享旨在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协调,并且常常基于结合了民族生态学方法的研究。
批评家指责该学科专注于地球欠发达地区的“前工业社会”。
民族科学原则强调社会如何理解自己的现实的重要性。为了了解文化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例如环境的分类和组织,民族生态学借鉴了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民族生态学是人类学家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社会如何概念化其周围环境,并可以确定社会认为其生态系统中“值得关注的”事物。该信息最终可用于环境人类学中的其他方法。
民族生态学是环境人类学的一个领域,它的许多特征都源于经典以及更现代的理论家。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是最早质疑单线进化的人类学家之一,他认为所有社会都朝着通往西方文明的同一,不可避免的道路前进。博阿斯强烈敦促人类学家从特质的角度收集详细的人种学数据,以了解不同的文化。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是另一位人类学家,其思想和理论影响着民族生态学的运用。Steward创造了“文化生态学”一词,这是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环境适应的研究,并着眼于相似社会中的进化路径如何导致不同的轨迹,而不是经典的全球进化趋势。这种关于文化进化的新观点后来被称为多线进化。Boas和Steward都认为研究人员必须运用主位立场,并且每个社会对环境的文化适应都不尽相同。此外,管家的文化生态学为民族生态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是人类生态学框架的另一个贡献者。怀特强调将文化解释为系统,并为解释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交以及将其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奠定了基础。这些人类学家共同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族生态学基础。Boas和Steward都认为研究人员必须运用主位立场,并且每个社会对环境的文化适应都不尽相同。此外,管家的文化生态学为民族生态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是人类生态学框架的另一个贡献者。怀特强调将文化解释为系统,并为解释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交以及将其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奠定了基础。这些人类学家共同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族生态学基础。Boas和Steward都认为研究人员必须运用主位立场,并且每个社会对环境的文化适应都不尽相同。此外,管家的文化生态学为民族生态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是人类生态学框架的另一个贡献者。怀特强调将文化解释为系统,并为解释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交以及将其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奠定了基础。这些人类学家共同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族生态学基础。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是人类生态学框架的另一个贡献者。怀特强调将文化解释为系统,并为解释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交以及将其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奠定了基础。这些人类学家共同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族生态学基础。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是人类生态学框架的另一个贡献者。怀特强调将文化解释为系统,并为解释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交以及将其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奠定了基础。这些人类学家共同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族生态学基础。
传统生态知识
传统生态知识(TEK),也称为土著知识,“是指土著和地方人民通过直接接触环境在数百或数千年中获得的不断发展的知识。” 它涉及特定社区通过与环境的关系而广泛持有的积累的知识,信念和实践。在这种情况下,TEK由社区在考虑诸如可接受的动植物使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的最佳方法,期望社会成员驾驭的社会机构等主题时的共同思想组成。 ,他们的世界观。
对TEK的研究经常包括对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理论划分的批评,将人类解释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例如,人类可以代表给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并且可以在创建,维护和维持其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可以促进成虫,种子传播和生物多样性波动等过程。它们还可以改变和调节野生或驯养物种中的动物行为。
传统的生态知识传统上一直侧重于西方科学可以从这些社区中学到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文化知识如何与科学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这种对生态适应的先前理解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态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社会中的本地知识在
民族生态学领域内,明确强调那些被视为“土著”,“传统”或“野蛮”的社会,这是整个20世纪人类学追求的普遍趋势。但是,社会存在于广泛的生物群落中,并且需要了解和理解除有害植物或如何获得最佳农作物以外的明确和当前存在的危险。克鲁克香克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许多人将传统生态知识视为“静态,永恒且密封的”概念。锁定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没有创新的机会,因此在后工业社会的新结构(例如美国)中是找不到的。
这样,民族生态学就可以存在而又没有其他概念的局限。例如,社会科学家试图了解城市青年使用的标记来识别对其生计的威胁,包括穿帮派颜色,纹身或穿上可能代表或成为武器的衣服的突起物。同样,关于社区的健康和需求的概念也随周围地区而散布。社会成员对如何在自己的国家,城市或邻里生活抱有一套信念,他们从小就认识到危险以及这些威胁来自何方。学科的扩展(人类生态学的边界)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将环境识别为动植物,
同样,社会科学家已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中使用民族生态学调查,以试图理解和解决与西方社会以及世界各地相关的主题。这包括研究人们在操纵周围世界时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和能力,尤其是他们的生存能力。
传统医学
传统社会通常通过利用当地环境来治疗医学问题。例如,在中草药中,人们考虑如何利用本土植物进行康复。
世卫组织表示,世界上将近80%的人口使用植物学方法作为疾病的主要治疗来源。面对现代气候变化,已提倡许多传统医学做法以实现环境可持续性,例如印度的阿育吠陀。
认识论的关注
根据多夫和卡彭特的说法,“环境人类学跨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分法,将自然类别(如旷野和公园)与文化类别(如农场和城市)之间的概念分离。”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固有的是,人类是违反先前原始环境的污染因素。
由于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了解人类如何为整个环境环境而努力,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样,在社会和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对应而不是对抗的关系的想法本身就令人困惑,并且违背了二十世纪前半叶普遍接受的理解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理解的自然与文化二分法继续受到诸如Darrell A. Posey,John Eddins,Peter Macbeth和Debbie Myers等人种学家的挑战。在西方科学的交汇中,对土著知识的认识也存在着一种整合方法,如果有的话。道夫(Dove)和卡彭特(Carpenter)辩称,一些人类学家试图通过“翻译,
与这种范式相反的是归因于命名法和认识论中的语言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仅此一个就创建了一个子领域,主要是对民族分类学的哲学的认可。但是,将种族分类法定义为新的还是不同的是不准确的。它只是对民族学长期以来的传统有了不同的理解,从而发现了不同民族用来描述其世界和世界观的术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寻求使用和理解这些知识的人们已经积极地使拥有信息的社会特许权和剥夺了公民权。海恩(Haenn)指出,在与环保主义者和开发商合作的几次案例中,
研究
在许多跨学科项目中,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检查土地使用情况,同时还要对社会科学背景进行调查。根据研究主题,可以使用民族生态学方法:如果生态系统的使用(影响)和特定的种族群体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技术之间存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