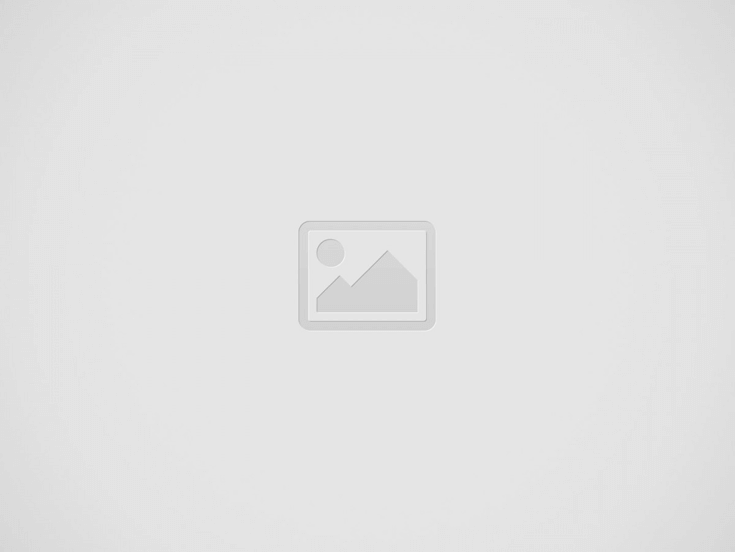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由拉尔夫·鲁戈夫 (Ralph Rugoff) 执导的第 58 届国际艺术展于2019年5月11日至11月24日举行。不确定、危机和动荡时期;“有趣的时代”,正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
展览一如既往地在两个主要历史遗址——贾尔迪尼城堡和军械库举行,但也涉及威尼斯各地的著名场地,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在这里举办,展览和附属活动也在这里举行。世界各地的未来形成了一条大而统一的展览路径,从花园中央馆到军械库,包括79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
本次展览的标题表达“有趣的时代”唤起了挑战甚至“威胁”时代的想法,但它也可能只是一种邀请,让人们始终看到和思考人类事件复杂性的过程,因此,邀请在由于墨守成规或恐惧而过于简单化的时代似乎尤为重要。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包括反映当今生存不稳定方面的艺术作品,包括对“战后秩序”的关键传统、机构和关系的不同威胁。但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艺术并不在政治领域发挥其力量。例如,艺术无法阻止民族主义运动和独裁政府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兴起,也无法减轻全球流离失所者的悲惨命运。
第 58 届国际艺术展突出了创作艺术的一般方法以及将艺术的社会功能视为包含乐趣和批判性思维的观点。展览聚焦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挑战现有的思维习惯,开启我们对物体和图像、手势和情境的解读。
这种艺术源于一种娱乐多种观点的实践:牢记看似矛盾和不相容的观念,并运用各种方式来理解世界。以这种方式思考的艺术家通过建议其他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语境中,从而为所谓的事实的含义提供了替代方案。他们的作品充满无限的好奇心和敏锐的智慧,鼓励我们对所有毫无疑问的类别、概念和主观性进行质疑。
艺术展览首先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它打算向我们展示艺术和艺术家,作为对所有过于简单化的态度的决定性挑战。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也许艺术可以成为如何在“有趣的时代”生活和思考的一种指南。它邀请我们考虑多种选择和陌生的有利位置,并辨别“秩序”如何成为多种秩序同时存在的方式。
中央展馆展览
展览从中央展馆(Giardini)发展到军械库,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79名参与者。自 1895 年第一届以来,作为双年展艺术展览的传统场地,Giardini 上升到威尼斯的东部边缘,由拿破仑在 19 世纪初制作。第一届(1895 年超过 200,000 名参观者,1899 年超过 300,000 名参观者)的成功引发了自 1907 年以来外国馆的建设,这些馆被添加到已经建成的中央馆中。贾尔迪尼现在拥有29个外国馆,其中一些由著名建筑师设计,如约瑟夫·霍夫曼的奥地利馆、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尔德的荷兰馆或由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梯形平面预制芬兰馆。
作为双年展场地展览重组的一部分,2009 年,位于贾尔迪尼公园的历史悠久的中央展馆变成了一个 3,500 平方米的多功能和多功能结构,成为其他花园展馆的永久活动中心和地标。它拥有由国际知名艺术家设计的室内空间,如 Massimo Bartolini(教育区“Sala F”)、Rirkrit Tiravanija(书店)和 Tobias Rehberger(咖啡馆)。
2011年,随着展览空间和入口大厅的重组,中央馆向多功能花园的改造完成。从那时起,中央馆可以为每个不同和众多的目的地享受最佳的空间和小气候条件,包括教育活动、研讨会和特殊项目。修复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完成了由威尼斯市议会于 2006 年发起的 Ottagonale 大厅的修复工作,并于 1909 年修复了伽利略奇尼圆顶内的画作以及装饰墙和地板系统的修复在威尼斯露台上。大厅,配备了所有接待公众的服务,因此,它以巨大的中庭形式成为展馆的一个支点,从中可以到达所有新的功能区域。
亮点
第四部分
劳拉·法瓦雷托
Lara Favaretto 的多方面艺术实践包括雕塑、装置和表演动作,通常通过黑色幽默和不敬来表达。在她的系列 Momentary Monuments (2009-ongoing) 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这不是为了美化任何历史事件,也不是为了培养民族认同感。法瓦雷托的纪念碑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更多的是悲喜剧,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腐烂、倒塌和溶解。这使得建造它们本身成为一座纪念碑的巨大努力是徒劳的。法瓦雷托作品中隐含的笑话是,即使是由最稳定的材料制成的物品,旨在永远凝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最终也会消失。
安托万·卡塔拉
Antoine Catala 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创造了新的有趣的关系。在探索错误传达的过程中,他试图发掘通过文字、符号、文本、表情符号(尤其是跨通信平台)传递意义的一些方式。通过他的文字作品和雕塑装置,他经常不假思索地关注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不是信息本身,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在中央馆的入口处,九块用彩色硅胶覆盖的大面板构成了作品It’s Over (2019)。随着空气从每个面板中缓慢抽出,浮雕文字浮出水面,传递出模棱两可的令人放心的信息:“别担心”,“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好”,“Tutto va bene”,“嘿,放松” ,或两只泰迪熊接吻的图像。在Arsenale 中,装置The Heart Atrophies (2018-2019) 提出了当代相当于中世纪的rebus,展示了人类如何一直与周围的标志保持密切、适应性和灵活的关系。
玛丽亚·洛博达
Maria Loboda 实践的核心是物体和图像通过它们的传输和相遇的轨迹不断转换。洛博达的作品激起了人们对所谓显而易见的不信任,但也邀请我们与他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事物——拥有的不确定性交朋友。Loboda 感兴趣的是图像如何受到它们传播的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凝视历史的塑造。
池田良司
作曲家兼艺术家 Ryoji Ikeda 的实践接近不朽的极简主义,经常将稀疏的声学作品与采用数字渲染信息的广阔领域形式的视觉效果交织在一起。这些整合形成了艺术家自己的广阔语言,它依赖于一种算法工作方式,其中数学被用作捕捉和反映我们周围自然世界的手段。
哈里斯·埃帕米农达
Haris Epaminonda 使用现成的材料,如雕塑、陶器、书籍或照片,她经常将这些材料结合起来,精心构建她的特色装置。这些物品被纠缠在一个公众不知道的历史和个人意义的网络中,可能对她来说也是如此。并不是她忽略了这些故事:它们是含蓄的,它们内在地发挥着自己的力量,当它们融入她的装置时,它们会轻轻地弯曲成不同的东西。她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品质,它们不可还原的体验品质,这使它们发光并变得可见。
妮可艾森曼
历史与现在、公开与隐私之间的回响为妮可·艾森曼的绘画和雕塑提供了背后的力量。她对当代生活动态的触角使她认识到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即世界上仍然充斥着被权力、暴食、贪婪、嗜血以及他们认为金钱是高于一切的价值所驱使的邪恶男人。
在她的雕塑作品中,艾森曼将这些力量描绘成可怕的、扭曲的、扭曲的、内脏的和癌变的。她对当下细节的坚定承诺,如火车上的周(2015 年)、晨间工作室(2016 年)和暗光(2017 年)、iPhone、牛仔裤、连帽衫、笔记本电脑、棒球帽和使用牛奶箱作为家具,将她牢牢置于现实主义和风俗场景的古老传统中:将艺术与生活隔开的膜尽可能地变得多孔。
奥古斯塔斯·塞拉皮纳斯
奥古斯塔斯·塞拉皮纳斯 (Augustas Serapinas) 对创造另类观点感兴趣,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多样性,这在机构和艺术界通常是缺乏的……他对“凑合”的创造力有着深刻的尊重,他的作品经常发现每天都有深刻的灵感。即使在他的家乡维尔纽斯的艺术学校,塞拉皮纳斯也突破了机构的限制,在学院内找到了一个隐藏的空间作为秘密工作室,并在一条注入维尔内勒河的海绵状水管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螺栓孔。 2012 年,他在维尔纽斯艺术学院的最后一年,他注意到一群孩子将周围的公共空间用作游乐区,并在他的工作室内建造了攀爬结构,让他们发现并融入他们的游戏中。
卡梅伦杰米
Cameron Jamie 的作品涉及多种媒体,从照片和视频到绘画、陶瓷、雕塑和影印杂志。然而,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让他受到最广泛关注的作品是 Kranky Klaus (2002-2003),一部记录了 Krampuslauf 阿尔卑斯山圣诞节传统的视频。在奥地利的一个乡村,晚上,男人打扮成角兽在街上掠夺,据说是在寻找据说淘气的儿童和年轻女性。Krampus 野兽是一种文化认可的编排仪式。
迈克尔·E·史密斯
Michael E. Smith 的雕塑、装置、视频和偶尔的画作充满了后人类的闹鬼感。艺术家通常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人们可能在垃圾场或最好的二手商店中找到的各种物品;这些人工制品的表面有证据表明曾被人手使用、磨损并最终损坏。他们被抛弃的事实本身就使他们充满了悲情,表明他们不受爱,无能,并被送入物质炼狱,在那里他们拒绝堕落或消失。在其他地方,实际死去的动物(或它们的一部分)进入了史密斯的雕塑词汇,仿佛是为了强调与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人造物体的死亡品质。
广告米诺利蒂
对于 Ad Minoliti 而言,形而上学绘画是现代主义乌托邦的象征,也是她认为其中一切可指责的象征:理想性的压抑性、刚性结构的保守性,甚至其隐含的二元逻辑,参考雅克·德里达的观点:西方思想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例如男性-女性、理性-情感或自然-文化。她的艺术努力是创造一个替代的表现空间来对抗这种现代主义的立场。她在玩具屋的想象世界中找到了形而上绘画空间的辩证异同体。
玩具屋是 17 世纪的发明,最初是作为一种教学工具而创建的,旨在指导女孩扮演家庭主妇、家庭管理员、生育孩子和丈夫支持者的角色,而男孩则接受这种分工和哲学. 米诺利蒂借鉴了玩具屋及其道具的美学,将其与现代主义意象相结合,呼应康定斯基、毕加索或马蒂斯,然后将其拆开、扭曲、移动并重新配置。
乔恩·拉夫曼
乔恩·拉夫曼 (Jon Rafman) 观察到,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乌托邦式的未来愿景盛行。然而,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愿景已成为反乌托邦的愿景。为了探索未来概念的这种转变,拉夫曼的作品采用了动态图像和计算机生成的图形,避开了有时与新技术相关的乐观主义。
阿瑟·贾法
三十年来,亚瑟·贾法在电影、雕塑和表演等媒介上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实践。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特定的黑色表现方式,以及如何从黑色存在的优势渲染世界(视觉上、概念上、文化上、地道上)的挑战——在它的所有欢乐、恐怖、美丽、痛苦、精湛技艺、异化、力量和魔法。Jafa 收集了基于网络的图像、历史照片、白话肖像、音乐视频、模因和病毒式新闻片段,以突出图像在种族恐惧中的荒谬和必要性。
尼尔·贝卢法
尼尔·贝卢法(Neïl Beloufa)——他的实践跨越电影、雕塑和装置艺术,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当人们理解现实及其表现时什么处于危险之中。他的做法拒绝采取任何权威立场;它在观察上既敏锐又不引人注目。
艺术家不断地将自己从他的主张中移开,好像在对观众说,“现在这是你的问题,你来处理它”。例如,为了观看全球协议(2018-2019)的视频,观众必须坐在让人联想到健身器材的结构上,这些结构不舒服并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同时,空间的配置意味着每个观众都可以观察其他人观察其他人:您可能正在观看视频,但总有人在看着您。
詹娜·卡德罗娃
Zhanna Kadyrova 艺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包括摄影、录像、雕塑、表演和装置,是她对形式、材料和意义的实验。她经常使用廉价的瓷砖做马赛克,并结合混凝土和水泥等重量级建筑材料。
中央馆展出的《二手》(2014 年至今)版本将威尼斯一家酒店的瓷砖重新用于制作服装和亚麻制品。对于 Market(2017 年至今,在Arsenale 展出),一个配备街头小贩所需一切的食品摊位,她用混凝土和天然石材制作香肠和意大利腊肠,并制作水果和蔬菜、香蕉、西瓜、石榴、茄子、厚实的马赛克。
郑伊安
Ian Cheng 使用计算机编程中的技术来创建由其变异和进化能力定义的生活环境。他正在开发“实时模拟”,即从基本的编程属性开始的有生命的虚拟生态系统,但可以在没有作者控制或结束的情况下自行进化。这是一种有意识地锻炼伴随无情变化的体验而产生的困惑、焦虑和认知失调的形式。
郑的最新生物,BOB(信仰之袋)(2018-2019),在中央馆展出,是一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形式,其个性、价值观和身体——让人想起蛇或珊瑚——不断成长. BOB 的行为模式和生活脚本由与人类的互动推动,人类能够通过 iOS 应用程序影响 BOB 的行为。鲍勃之后的生活:第一卷(2019 年),在军械库中呈现,作为对以鲍勃为中心的叙事宇宙的一种“预览”。
奈里·巴格拉米安
Nairy Baghramian 融合机械和拟人形式,创造出令人费解的雕塑作品。她的作品将雕塑设想为一种混合生物。巴格拉米安的物体既不是完全机械的也不是完全有形的,很难确定。 Dwindlers 是沿军械库外部走廊展出的一系列玻璃附属物,迫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看什么?损坏的通风管道或巨大的肠子的集合?装饰性装饰或毁灭性的结构?”。
在中央展馆,她展示了“维护者”(2019 年),这是一幅由相互依存的雕塑元素组成的拼贴画,它们紧密组合在一起(生的铸铝紧紧压在蜡模上,由软木条和涂漆支架支撑)。坚固而顽固的形式拼贴在材料支持和攻击之间形成了动态张力——如果没有软木塞和涂漆支架,作品可能会崩溃。
朱莉·梅雷图
Julie Mehretu 早期的画布提到了地图、建筑图和城市规划网格;艺术家使用了一系列指向全球流动性和全球不平等的矢量和符号。他们在使用尺度和负空间方面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它们传达了一种速度感。在她最新的画作中,她拥抱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迷失方向,在作品中添加和删除了喷枪笔触和丝网印刷元素,唤起了一种消散和失落的感觉。尽管观众无法再将底色的细节作为图像信息提供给观众,但该源图像仍然能够在情感层面上进行记录,为完成的绘画定下基调。
亨利·泰勒
亨利泰勒将他的绘画实践描述为“贪婪的”,他的作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题,从一贫如洗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无论是通过对家人和朋友的亲密肖像,还是通过将不同地域和历史拼接在一起的政治影响群体场景,泰勒的目标都是诚实地描绘黑人经历的现实和美国生活中经常不公正的运作。但是,尽管他对不公正现象的敏锐洞察力和艺术史参考的频繁结合,泰勒的照片并不沉重。他们大胆的形式和块状颜色是直接的,吸引了观众。
吉米达勒姆
吉米·达勒姆 (Jimmie Durham) 的创作还融入了写作和表演元素,最常采用雕塑的形式,将各种日常用品和天然材料组合成生动的形式。达勒姆所说的“与被拒绝物体的非法组合”的生产过程,可以看作是充斥在他的作品中的颠覆态度的体现。
在中央展馆达勒姆展示了黑色蛇纹石,这是一块由不锈钢框架环绕的大块同名岩石——半吨重的质量在其顽固的毅力中反抗。在军械库中,由家具部件、光滑的工业材料或旧衣服组合而成的每件雕塑都近似于有名无实的动物的规模——然而,由此产生的形式并不是生物的肖像,而是挑战传统启蒙运动观念的诗意纠缠人与自然的分离。
鲁拉·哈拉瓦尼
鲁拉·哈拉瓦尼 (Rula Halawani) 幽灵般的照片捕捉到了将她的国家变成战区的周期性暴力事件的后果。凭借她作为摄影记者的背景和她对以色列占领下的生活的回忆,哈拉瓦尼在现在陌生的风景中寻找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逐渐消失的痕迹。通过摄影这一媒介,占领的空间含义不仅通过建筑环境中政治结构的表现来体现,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负空间和阴影幻觉的空虚中。
苏哈姆·古普塔
在他幽灵般的肖像中,Soham Gupta 照亮了加尔各答的夜生活,揭示了这座城市一些最脆弱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在他的系列焦虑中,我们跟随这些夜间活动的人物在他们居住的世界中穿行,成为摄影师想象中的生动人物。古普塔认为他的肖像是一个协作过程的结果,来自他和他的主题彼此信任的亲密互动。摄影师对社会边缘的人有着本能的亲和力;他走在他们中间,认同他们的痛苦和挣扎。
花时间研究每个主题后,古普塔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传记。古普塔的照片为无能为力的人注入了表现力。这些照片不仅仅是对城市及其人民的记录,而是一种植根于更重要事物的心理状态的表达。一种脆弱和孤独感被欢乐和自发的时刻所打断。虽然痛苦的哭泣和痛苦可能会被摄影图像所掩盖,但古普塔的照片生动地表达了只能在夜间才能看到的人性的各种阴影。
李布尔
在韩国军事独裁统治期间,作为左翼活动人士的女儿长大,李布尔在一个经历快速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国家经历了专制政权的影响。她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后期,是街头表演,她制作并穿着可怕的“软雕塑”服装,服装上装饰着突出物和悬垂的内脏。随后,她将女性身体中的半机械人雕塑变成了机器,形成了没有头部和四肢的不完整的混合体。他们反过来又引导她探索受日本漫画和动漫、生物工程和布鲁诺·塔特 (1880-1938) 富有远见的建筑中所构想的梦想、理想和乌托邦启发的未来主义城市景观的想法。
劳拉·法瓦雷托
Lara Favaretto 的多方面艺术实践包括雕塑、装置和表演动作,通常通过黑色幽默和不敬来表达。在她的系列 Momentary Monuments (2009-ongoing) 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这不是为了美化任何历史事件,也不是为了培养民族认同感。法瓦雷托的纪念碑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更多的是悲喜剧——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腐烂、倒塌和溶解。这使得建造它们本身成为一座纪念碑的巨大努力是徒劳的。法瓦雷托作品中隐含的笑话是,即使是由最稳定的材料制成的物品,旨在永远凝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最终也会消失。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 (Lawrence Abu Hamdan) 将自己描述为“私人耳朵”,专注于聆听的政治、声音的法律和宗教影响、人类的声音和沉默。他的实践源于 DIY 音乐的背景,但目前涵盖电影、视听装置和现场音频散文,他更喜欢“演讲表演”这个词,因为它更好地描述了声音和内容的交织,以及话语及其发表的条件。他将人类的声音视为一种政治化的材料,政府或数据公司很容易掌握。
第五部分
特蕾莎·马戈勒斯
特蕾莎·马戈勒斯 (Teresa Margolles) 用女权主义的视角来观察遍及她的祖国墨西哥的毒品暴力的残暴行为。Margolles 研究过法医学并共同创立了受死亡金属启发的艺术家集体 SEMEFO,在她的整个实践中,Margolles 一直将政府疏忽、毒品定罪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以及特定的质地、气味和身体残骸作为主题。
孙原&彭宇
艺术家孙原和彭宇夫妇于2000年开始合作。2009年,他们创作了装置孙原彭宇,这是一幅描绘他们艺术联盟关系和动态的自画像。一个反复出现的烟圈被一把由机械臂驱动的扫帚持续地驱散,扫帚在空中不停地扫荡;烟雾会不断地重新出现,直到扫帚再次撞击时才消散。
对孙和彭来说,这两种成分相遇的那一刻,又一次消融,象征着他们工作方式中共同艺术创作的时刻。几乎孙原和彭宇的所有装置都致力于吸引观众的奇迹和紧张感。观看观众的行为是他们近期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作品通常涉及到令人生畏的眼镜表演。
克里斯蒂安·马克莱
Christian Marclay 的作品是由已经存在的物体、图像和声音制成的,他对这些物体、图像和声音进行了挪用和操纵。他对声音和图像之间关系的探索使他将采样技术应用于好莱坞电影。他创造了剪辑的蒙太奇以形成新的叙事和多屏幕投影。
他使用找到的物体、图像和声音,并将它们拼贴在一起,并试图用现有的东西创造一些新的和不同的东西。完全原创并从头开始似乎总是徒劳的。他更感兴趣的是把已经存在并且是我周围环境一部分的东西切碎,扭曲,把它变成不同的东西;通过操纵和并置来挪用它并使其成为他的。
弗里达·奥鲁帕博
Frida Orupabo 的主要关注点是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描绘,特别是因为它与媒体文化中的图像流通有关。她结合从她的个人档案中找到的照片和图像,创建了探索种族、性别、身份、性、凝视和殖民暴力等主题的数字拼贴画。Orupabo 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和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她最初开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上传和流式传输她的拼贴画,以此作为获取源材料和干预构建艺术史产生的黑人女性身体的无休止图像循环的一种手段,殖民主义、科学和流行文化。
西普里安·盖拉德
Cyprien Gaillard 将人造和自然的熵作为他的中心关注点,通过他的视频、雕塑、摄影、拼贴画和公共艺术对进步的想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作为一名游牧观察者,Gaillard 在城市环境和自然景观中跋涉,寻找嵌入周围环境的深层时间迹象。他将外部世界的碎片带入内部,形成不合时宜的并列,结合破坏与重建、更新与退化的意象。
盖拉德的实践是腐朽的视觉考古学,无论是物理形式的侵蚀还是社会和历史意义的侵蚀。盖拉德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崩溃时间,他与废墟的浪漫主义作斗争,暗示了一种无私的凝视,通过这种凝视,可以通过循环时间的统一框架来理解事件和地点的残余。
武丹
Danh Vo 为 2019 年艺术双年展设计的不拘一格的合作者圈子包括他的男朋友、他的侄子、他的父亲和他的前教授。在 Vo 的装置中,历史与艺术家自己的传记相遇,通过带电的象征物,如文化图标或受损的宗教意象,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文字和隐喻参与。
斯拉夫人和鞑靼人
Slavs and Tatars 成立于 2006 年,最初是一个读书俱乐部,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艺术家团体,其多方面的实践仍然非常接近语言,无论是文字还是比喻方式。他们的作品,从雕塑和装置到演讲表演和出版物,是一种非传统的研究方法,用于研究被两个象征性和物理屏障包围的地理区域的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前柏林墙和中国长城。这片广阔的土地是东西方碰撞、融合并重新定义彼此的地方。
刘伟
刘伟的早期作品经常涉及城市建筑、城市景观和日常物品,并通过在绘画和装置中反复出现的几何图式来表现物理世界的各个方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从牛皮狗咬到书籍,从家用电子设备到中国瓷器和废弃的建筑材料。他最近的大型装置唤起了现代主义舞台布景的正式和辉煌,充满了几何形状和形式。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的作品沉浸在他家乡泰国的社会生活、多元文化和动荡的政治之中,而睡眠、做梦和记忆的短暂领域则作为探索、解放和安静颠覆的空间重现。这些主题融入了《同步》(2018 年)的光、声和屏幕的复杂相互作用中,该作品由日本艺术家久门刚(1981 年,日本)制作,并在军械库中展出,在其环境中,韦拉斯哈古的门槛空间被赋予了物理形式。
中央馆的两件作品标志着韦拉斯哈古的重大转变,他第一次在泰国以外的哥伦比亚工作,为他目前的项目记忆。哥伦比亚的地形和几十年内战留下的伤痕对韦拉斯哈古有着内在的亲和力。日常生活结构的集体记忆部分的创伤,就像在纳布阿一样。
Handiwirman Saputra
在过去的十年里,Handiwirman Saputra 创作了一系列神秘的雕塑和绘画,题为“无根无芽”,由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随机物体引发。其中一些作品的动力来自他家附近的一条河流,那里裸露的竹林和树木的根部与家庭垃圾纠缠在一起。Saputra 不仅对他在那里发现的事物感兴趣,而且对它们之间的关联感兴趣。
克芒瓦勒胡莱尔
Kemang Wa Lehulere 丰富层次的作品鼓励游客聚集在它周围共同沉思。这种集体的概念是艺术家更广泛实践的关键:在开普敦担任活动家多年后,他在 20 多岁时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他于 2006 年创立了 Gugulective,这是一个表演和社会干预的艺术平台。
在军械库和中央馆展出的装置都是由从课桌椅上回收的木材和金属制成的。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汇集在一个由关联、参考和故事组成的网络中,因为对于 Wa Lehulere 来说,个人传记和集体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高里吉尔
到更远的地方旅行,吉尔看到了新的郊区“存在于一片废墟中的殖民地,模仿英国城堡,周围是移民劳工的临时房屋”。她的建筑面无表情包括开发商兜售无法实现的梦想的囤积;关于建筑和施工的教育展示;种植在真树中的假棕榈;主持空调机组的女神;圣雄甘地路上一座正在拆除的新建筑,上面覆盖着撕裂的布片;大干道旁一堆堆腐烂的垃圾;到处都是毫无特色的高楼。
迈克尔·阿米蒂奇
迈克尔·阿米蒂奇 (Michael Armitage) 的画作介于幻想现实和现代生活的政治混乱之间,将多个叙事线索编织在一起。作为复杂社会动态的敏锐观察者,他通过叙事绘画的语言颠覆了传统的表现方式。放大不平等和政治不确定性的问题,他生动画面的如画之美掩盖了一个险恶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奢华的细节和充满活力的色彩的碰撞提供了对支配内罗毕日常生活的社会习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洞察。
杰西·达林
杰西·达林 (Jesse Darling) 的雕塑受过伤、心烦意乱、摇摇欲坠,但它们也充满生机。这些不起眼的组合由低成本的日常材料制成,唤起了具有不寻常辛酸的身体;它们也绝对不是纪念性的。由于神经系统疾病无法使用大部分右臂,Darling 被遗传的意识形态和能干的男子气概所震惊,这些思想最初影响了他们对雕塑的理解:“努力工作”和“手势”的想法。
钦哲诺布
在钦哲诺布作为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的作品中,背景的哲学问题起着核心作用。有人建议,理解和解释总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有更广阔的视野。在佛教界被称为宗萨钦哲仁波切的诺布是一位西藏和不丹喇嘛,因其教法和写作而受到尊重。
亚历山德拉·伯肯
Alexandra Bircken 的实践围绕着人类形态而建立。她的作品采用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材料,从硅、尼龙紧身裤、武器和机械等制成品,到羊毛、皮革、树枝和干果等有机材料。剥夺了它们以前的目的,这些被组装成非凡而令人不舒服的安排,每一个都在相反的紧张局势中活跃起来。
在中央展馆,伯肯展示了六件作品,它们交织了性别、权力与脆弱、动物与机器等主题。这些作品唤起了我们的脆弱性、我们的肉体,以及我们为保护自己免受外界和彼此伤害而创造的傲慢工具。在军械库中,艺术家们展示了本能的、世界末日的、动态的装置 ESKALATION (2016),这是对人类终结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反乌托邦观点。
纳布其
纳布其致力于探索雕塑物体的美学和材料方面;对艺术家而言,通过忠实保留原始品质的人造物品的组合来实现对户外的模仿是很重要的:“我想恢复材料的初始状态和属性,而不是用自己的双手妥协这些。这意味着不在展览空间展示精心创作的艺术品。我还想构建一个与室外(外部)和内部(内部)相关的环境。
这里使用的所有材料本质上都是装饰性的,据说是在模拟或刺激一种现实,或者培养一种美学的想象力:一种虚拟的美学,令人愉快和好客“。这种对现实的再创造能被感知为现实的一部分吗?它是否会在观众中引发与真实遭遇一样的情感共鸣?她的作品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希尔帕·古普塔
希尔帕·古普塔 (Shilpa Gupta) 围绕边界的物理和意识形态存在展开工作,揭示它们同时具有任意性和压制性的功能。她的实践借鉴了民族国家之间的间隙区域、民族宗教分歧和监视结构——在合法与非法、归属与孤立的定义之间。日常情况被提炼成简洁的概念性姿态;作为文本、动作、物体和装置,古普塔通过这些表达了潜移默化的力量,这些力量支配着我们作为公民或无国籍人的生活。
安德拉·乌苏萨
强迫症和暴力欲望;屈服于性和政治统治;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作为建筑和虚构的身份:这些是巩固安德拉·乌苏扎 (Andra Ursuţa) 的雕塑和装置中探索的虚无主义和悲喜剧场景的一些主题。艺术家的作品以悖论和讽刺为基础,利用政治事件、陈词滥调和寓言以及个人记忆,试图揭露和破坏权力动态,这种动态使侵犯与平庸、冷漠与同情、卑鄙与同情之间的危险界限永久存在。幽默。
克里斯汀和玛格丽特·韦特海姆
Christine 和 Margaret Wertheim 的 Crochet Coral Reef 介于雕塑和学习设备之间,是一种植物学、生物模型。这种三维模型曾经是用玻璃制成的;在 Wertheims 的项目中,这些表格是用钩针编织而成的。纱线、线、金属丝、旧录像带、珠子、一针一针,逐渐组合成一系列珊瑚礁。科学与艺术的优雅结合,钩针珊瑚礁反映了双胞胎的传记:玛格丽特,受过物理学家训练,是一位著名的科学作家;克里斯汀是一位诗人和前画家,是一位批判性研究教授。
2005 年的一天晚上,在 Wertheim 姐妹的客厅里,克里斯汀凝视着散落在咖啡桌上的羊毛形状,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钩编珊瑚礁!”。玛格丽特在网上发布了加入该项目的邀请,邮件中开始出现大小模型,与姐妹们制作的表格相结合。出现的是一个广阔的命题:钩针珊瑚礁是一种需要并代表时间和想象力以及无等级合作的东西。迄今为止,已有超过 10,000 名参与者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共同编织了 40 多个卫星礁。
姜锡京
结合绘画、雕塑、视频以及艺术家所说的“激活”,Suki Seokyeong Kang 的多元实践集中在当今个人的位置和角色上。康利用韩国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以及她自己的个人历史来重新构想意识形态结构,并设想政治化的舞台,在这些舞台上,授权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在当下的时空中表达和行使他们的能动性。
奥托邦恩康加
Otobong Nkanga 的作品参考了矿物、能源、商品和人员的(通常是暴力的)运动和交换,提醒人们物体和行为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有联系,总是有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静止的”,这位艺术家说。“身份在不断演变。非洲的身份是多重的。例如,当我审视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肯尼亚、法国或印度文化时,如果不谈论殖民影响和这种交流的影响,就无法谈论特定的身份– 贸易、商品和文化”。
亚历克斯·达科尔特
Alex Da Corte 的身临其境的作品证明了一种磁性的世界创造行为。 他编排了一种象征和暗示的对象的舞蹈,而不是那些东西。 他通过代码和符号讲述故事,在其中,大量挪用、组装、上演和精心制作的美国风同时注入了高尚和低俗的文化参考和一元店的发现。
在中央展馆,观众成为巨人,看着人们在 The Decorated Shed(2019)的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这是一个微型美国郊区村庄的精确复制品——来自流行的电视连续剧《罗杰斯先生的邻居》——呈现在联邦-风格的桃花心木桌,加上企业连锁餐厅标牌。在Arsenale 中,霓虹灯下的橡皮铅笔恶魔将观众微型化,让他们坐在长椅上观看超大和超饱和的成人版熟悉的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中,一系列角色表演着催眠般缓慢的编舞。
第六部分
哈利尔·阿尔廷代尔
Halil Altındere 在他的视频、照片、装置和绘画中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作为社会政治机制及其对个人的侵犯的敏锐观察者,他经常使用民族国家制度来维护权威和限制差异的方式。身份证、邮票、钞票、报纸头版、军国主义口号和政治领导人的照片被挪用,以颠覆社会或政治操纵和正常化。
来自库尔德人的背景,并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冲突的高峰期长大,Altındere 在许多作品中都谈到了对少数民族的忽视和虐待。近年来,Altındere 在多部作品中参与了全球难民危机,包括《太空难民》(2016 年),该系列的灵感来自艺术家与叙利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宇航员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法里斯的会面,后者与苏联团队一起前往太空。 1987 年。
尹秀珍
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尹秀珍一直致力于使用回收材料创作充满社会参考意义的雄心勃勃的雕塑。反映过度发展、消费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 1989 年后的中国,在她的作品中,她将柔软的纺织品与一系列物品——通常具有截然不同的质地和内涵——如手提箱、混凝土碎片、碎片、金属和工业对象。
卡罗尔·博夫
Carol Bove 的雕塑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简洁线条。她的正式句法是弯曲、凹痕、扭矩、扭结、皱褶、折痕和其他褶皱的熟练语言,这些褶皱使雕塑表面充满活力。艺术家将这些作品称为“拼贴雕塑”,这是一种在工业形式和刚刚发现的、过时的和新造的之间寻找生产张力的活动。
她的材料的物理摩擦通过红色、黄色、粉红色和绿色的大胆糖果色调色板与她粗糙的未经处理的钢材形成动态对比。她的油漆罐的光滑表面与她发现的物体粗糙的褪色物质。在这种模式下,表面颜色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她的钢管是由柔软的、可延展的物质构成的。Bove 巧妙的扭曲、折叠和弯曲要求观众采用动觉方法:它们迫使身体、眼睛和思想移动、移动和环绕作品。如果这些物品要讲述一个故事,那将是对运动和压力、力量和柔软度的描述。
艾弗里·辛格
艾弗里·辛格 (Avery Singer) 的画作探索了媒介的极限。她没有使用画笔绘画,而是使用 SketchUp(一种深受建筑师和工程师欢迎的 3D 建模软件)来创建数字构图,然后将其投影和喷绘在画布上。通过描绘性别中立的面孔和非性别化的形状,辛格通过将面部特征减少为一系列线条、网格和几何形状来突出身份的模糊性。
在过去的两年里,辛格为她的灰色调色板引入了色彩。糖果色的 Calder (Saturday Night) (2017) 以及一组与中央展馆中呈现的柔和、半抽象的图片形成对比的画作。在挑战表现的极限的同时,辛格不断寻求扩大绘画的可能性,同时也与关于艺术家性别的还原理论和假设作斗争。
恩吉德卡·阿库尼利·克罗斯比
Njideka Akunyili Crosby 的画作反映了她作为当代尼日利亚侨民成员的经历,描绘了许多人不熟悉的特定文化和民族身份,尽管那些走类似道路的人一眼就能认出。青少年时期移居美国留学的阿昆伊利·克罗斯比(Akunyili Crosby)自信地(尽管也许并非没有内在摩擦)在不同的审美、知识、经济和政治背景之间移动,正是这些背景的碰撞和错位赋予她的画作紧张和辛酸。
这位艺术家画肖像画和家庭室内装饰,通常以她和她的家人为特色。这些场景既平坦又无限深,窗户和门口通向其他空间,而这些图片中描述的空间是不确定的;某些细节——例如铸铁散热器——表明寒冷的气候(例如纽约,艺术家曾居住过一段时间),而其他细节,例如放在桌子上的石蜡灯,则取自 Akunyili Crosby 的作品尼日利亚的回忆。
安东尼埃尔南德斯
Anthony Hernandez 的摄影作品艰苦而朴素。在过去的三年里,一个普遍的问题困扰着摄影师:如何描绘城市的当代废墟以及城市生活对弱势公民的严酷影响?埃尔南德斯通过关注摄影师刘易斯·巴尔茨所说的“失败者的风景”来解决这个问题——无家可归者营地、失业办公室、汽车报废场、公共汽车候车亭,以及在城市郊区发现的其他被忽视的空间。埃尔南德斯的作品既不浪漫也不怀旧,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对幸福的承诺已经变质的地点和空间。
赞妮尔·穆霍利
Zanele Muholi 以作品 Faces and Phases(2006 年至今)而闻名,这是一部不断发展的南非黑人女同性恋肖像档案,Zanele Muholi 是一位极力反对沉默和隐身的摄影师。更喜欢被称为“视觉活动家”而不是艺术家,Muholi 是女性赋权论坛以及 Inkanyiso 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酷儿和视觉激进主义平台。
自我表现的重要性是 Somnyama Ngonyama 的核心,黑狮万岁(2012 年至今),这是一系列毫无歉意的自画像,艺术家打算将这些自画像构建成 365 幅南方黑人女同性恋生活中一年的图像非洲。该系列包括在军械库展出的艺术家挑衅或直接与观众的目光相遇的作品,以及在中央展馆展出的穆霍利避免和挫败它的较小的银色明胶版画。
斯坦·道格拉斯
斯坦·道格拉斯 (Stan Douglas) 的电影、录像、照片和电影装置通常涉及他所谓的“投机历史”,描绘事件可能发生截然不同的转折的关键时刻。道格拉斯认为照片“就像没有运动图像的电影”,并以与电影中的场景大致相同的方式创建它们。他重演特定的事件,对它们进行长期的研究,然后用布景、演员和细致的灯光重新上演。
Korakrit Arunanondchai
Korakrit Arunanondchai 在表演、视频和装置之间工作,创造了一个家庭、迷信、灵性、历史、政治和艺术交织在一起的区域。他与历史相互关联的系列始于 2013 年,房间里挤满了有趣的名字。反复出现的中心人物,一位虚构的泰国画家,被描绘在反映传统信仰、自然环境和技术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境中,不断变化的泰国的政治和文化。
中央馆展示的雕塑装置是一系列“后自然”的树状形式,而军械库则有一个由亚历克斯·格沃伊克(Alex Gvojic,1984,美国)制作的三屏装置。画廊被装扮成潜力和聚集的空间。最近,他建造了不可思议的森林环境:可能在人类世幸存下来的类似老鼠的生物的栖息地。
埃德·阿特金斯
埃德·阿特金斯(Ed Atkins)制作了各种自画像的卷积。他写了令人不舒服的私密的、椭圆形的预言,画了可怕的漫画,并制作了逼真的计算机生成的视频,这些视频通常以男性人物处于无法解释的心理危机的阵痛中为特色。在军械库中,装置 Old Food (2017-2019) 充满了历史性、忧郁和愚蠢。在这里,阿特金斯扩展了他的情绪领域,通过更广泛的问题和引文来缓和影响自传的形象。
构成 Bloom 的图画(编号为 1 到 10 并在中央展馆中展示)的特征是狼蛛正在下船试探性的手或以其他方式栖息在摆姿势的脚上,每张图都有 Ed Atkins 缩小的头部,蜘蛛的腹部应该在那里。阿特金斯的脸被蜘蛛毛包裹着,打破了第四面墙,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脸上带着矛盾的、可疑的意识表情。
加布里埃尔·里科
作为废弃文物的收藏家、自称为本体论者、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和对动物有亲和力的人类经验研究人员,加布里埃尔·里科可以说是有“饥饿的眼睛”。他的质疑、探索和收集导致了一种后超现实主义/贫穷艺术的方法,该方法挖掘了一系列材料,从动物标本和自然物体到霓虹灯形状和其他人造物品的残余物。这产生了发人深省的雕塑,解决了环境、建筑和未来文明废墟之间的关系。
在 Rico 的所有作品中,故事的美在于细节。这些组成部分反映了特定地点墨西哥面临的挑战,同时与我们共同的全球关注产生共鸣。Rico 在形式上和哲学上都考虑了空间的脆弱性,呈现了现在的不稳定时刻。
阿妮卡·伊
破坏有机与合成、科学与虚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阿妮卡·易 (Anicka Yi) 多变的创作以艺术家所描述的“感官生物政治”为基础。Yi 的新工作集中在最近对“机器生物化”的调查上,她专注于机器的感觉系统,并思考如何在人工智能 (AI) 实体和有机生命形式之间建立新的沟通渠道。
卡利尔约瑟夫
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 Kahlil Joseph 的混合实践跨越了电影、视觉艺术和文化媒体,在主流和博物馆之间的水域中顺畅地航行。他引人入胜的电影和身临其境的视频装置打破了上流文化与下流文化、电影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任何二分法。
安德烈亚斯·洛利斯
Andreas Lolis 用大理石创造了错视效果。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创造了一系列地板雕塑,模仿他在街角或公园长椅上看到的短暂物体——超现实的垃圾袋、纸板箱和木箱。许多这些雕塑都有明显的磨损迹象——它们的表面被压碎或弄脏、碎裂或破碎。通过在高度古典的媒介中复制碎屑,他有意破坏传统的价值和地位体系。Lolis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只与大理石一起工作,他将他与这种材料的关系描述为虔诚的。他对细节的高度关注意味着每个真人大小的物体几乎都能欺骗眼睛。
托马斯·萨拉切诺
托马斯·萨拉切诺 (Tomás Saraceno) 的研究受到无数世界的滋养。他的 Arachnophilia Society、Aerocene 基金会、社区项目和互动装置通过连接学科(艺术、建筑、自然科学、天体物理学、哲学、人类学、工程)和敏感性探索了居住环境的可持续方式。
在所有这些项目中,萨拉切诺与我们周围存在的生命形式互动,在生态动荡的时代,它鼓励我们将我们的观点与其他物种和系统相协调,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从蜘蛛群落到引力波浪,并以混合和替代的方式居住在我们共享的星球上。
玛丽亚·洛博达
Maria Loboda 实践的核心是物体和图像通过它们的传输和相遇的轨迹不断转换。洛博达的作品激起了人们对所谓显而易见的不信任,但也邀请我们与他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事物——拥有的不确定性交朋友。Loboda 感兴趣的是图像如何受到它们传播的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凝视历史的塑造。
塔瑞克·阿图伊
Tarek Atoui 的实践将音乐与当代艺术联系起来,通过参与式和协作式的声音表演扩展了聆听的概念。受 1960 年代艺术家所呈现的开放形式的影响,扩大了对音乐的理解并使其更接近视觉艺术领域,Atoui 构思并协调复杂的环境以培养声音。通过他的装置、表演和合作,他打破了表演者和观众对表演的预期概念,提出了多种体验方式:视觉、听觉和身体。
安西娅·汉密尔顿
Anthea Hamilton 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疏离感。流行文化、时尚和设计中的复古参考打开了身临其境的环境和不可思议的物体,它们的原始含义在她的雕塑和装置中被清空和转化。与过去几十年的艺术和文化的时间距离可能会产生误导:时间的流逝会使某些参考文献变得庆祝、媚俗甚至中性。
在 Hamilton 的作品中,重新考虑了时尚和设计的良性元素。在之前的作品中,她借鉴了历史悠久的设计师、名人和标志性时尚潮流,以放大它们的影响,并将它们彻底颠覆。挑衅是通过重复和空白和表面的部署而产生的。结果几乎是幽闭恐惧症,压抑汉密尔顿的转变所揭示的欲望。
杰佩·海因
Jeppe Hein 的改良社交长椅鼓励通过从玩耍到休息的各种活动进行探索和实验。它们是对任何决定身体在空间中运动的建筑工具的反作用。对于 Giardini,艺术家制作了一组四张长凳,它们似乎是从青色泻湖中生长出来的,像玩具火车轨道一样在空中盘旋。位于巴西、波兰和罗马尼亚馆之间的草坪上,威尼斯的改良社交长椅(2019 年)为社交互动创造了空间,并邀请减速。
其他设施
贾尔迪尼国家馆
除了今天的中央馆,其第一个核心建于 1894 年,此后多次扩建和修复,在大公园内还建造了 29 个展馆,由参展国家在不同时期建造。这些亭子被公园的绿色环境所包围,代表了 20 世纪建筑的高价值,以许多高管的名字命名,包括阿尔托、霍夫曼、里特维尔德、斯卡帕和斯特林。
双年展图书馆
自 2009 年以来,双年展图书馆是贾尔迪尼中央展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修复工作于 2010 年随着大型阅览室的开放而完成,周围环绕着一个两层画廊,上面布置了 800 多米的书架。阅览室也用于会议和研讨会。
图书馆专门研究当代艺术,特别注重记录和深化基金会的活动,保存双年展活动的所有目录并收集与建筑、视觉艺术、电影、舞蹈、摄影、音乐、戏剧学科相关的书目材料.凭借超过 151,000 册和 3,000 种期刊的书籍遗产,它是意大利领先的当代艺术图书馆之一。
图书馆的遗产源自ASAC 图书档案,通过购买、捐赠,尤其是与当代、国家和国际艺术的主要生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交流,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自2009年以来,图书馆还通过图书馆欢迎和收购参加艺术展览和建筑展览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捐赠的书籍。由双年展基金会实现的这个项目所收集的书籍是与艺术和建筑展览馆长不断合作的结果。
书店
Giardini 的图书馆由艺术家 Rirkrit Tiravanija 设计,是一个小巧实用的空间,没有多余的细节和装饰。
自助餐厅
由 Tobias Rehberger 设计并根据特定的绘画风格 Razzle Dazzle(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舰上使用)进行绘画,自助餐厅是一个坐下来寻找点心的地方,也是一个让自己(愉快地)迷失方向的地方编织相互交错的对比色几何形状,创造出复杂而生动的光学图案。
一个自助餐厅的艺术作品,其设计的“Was du liebst”,使 Rehberger 荣获 2009 年艺术双年展最佳艺术家金狮奖。
2019 威尼斯双年展
第 58 届威尼斯双年展是于 2019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每两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一次。艺术总监拉尔夫·鲁戈夫(Ralph Rugoff)策划了其中央展览“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90个国家贡献了国家馆。
威尼斯双年展是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国际艺术双年展。经常被描述为“艺术界的奥运会”,参加双年展对当代艺术家来说是一项享有盛誉的活动。这个节日已经成为一个展览的星座:由当年的艺术总监策划的中央展览,由各个国家主办的国家馆,以及整个威尼斯的独立展览。双年展上级组织还定期举办其他艺术节:建筑、舞蹈、电影、音乐和戏剧。
在中央国际展览之外,个别国家制作自己的展览,称为展馆,作为他们的国家代表。拥有展馆建筑的国家,例如位于 Giardini 的 30 座展馆,也需自行承担维护和建设费用。没有专门建筑的国家会在威尼斯军械库和整个城市的宫殿中建造展馆。
La Biennale di Venezia 成立于 1895 年。Paolo Baratta 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担任主席,在此之前从 1998 年到 2001 年。La Biennale 站在研究和促进当代艺术新趋势的前沿,组织展览、节日和研究在其所有特定领域:艺术(1895 年)、建筑(1980 年)、电影(1932 年)、舞蹈(1999 年)、音乐(1930 年)和戏剧(1934 年)。它的活动记录在最近经过全面翻新的当代艺术历史档案馆 (ASAC) 中。
在所有领域,都有更多面向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研究和制作机会,直接与知名教师接触;通过国际项目双年展学院,这变得更加系统和连续,现在在舞蹈、戏剧、音乐和电影部分运行。